
登录后畅享更多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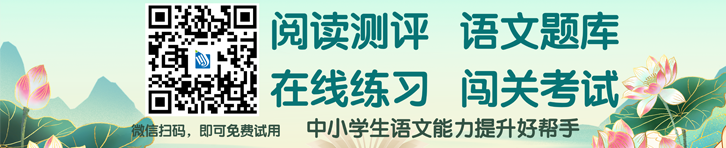
好人是之
郭启宏
于是之卧病多年。期间曾住过中医院,虽不辨识探视者,犹能眼观电视里《茶馆》的画面,手指自己“哦哦”几声;今年春上我去协和病房看望,他沉疴绵惙,已经连电视也不能看了。回想起当年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舞台形象,从《龙须沟》里程疯子听知小妞子淹死时倚门搓泥的神情,到《茶馆》里粘贴“莫谈国事”后摩挲着双手走路的步态,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酸痛,岂止是人世无常的浩叹,更有文化层面的惆怅……
自从熟悉了于是之,我情愿回归荒诞的史学经典:世上只分好人和坏人,且带相,就像《镜花缘》所描绘,好人脚下一朵红云,坏人则一团黑气,望之即知,免得上当。
我于1989年从北昆调入人艺。此前,我正经历着一段人生坎坷路,我当然愿意进入这座辉煌的艺术殿堂。如果记忆无误,从问题的提出,到调动的完成,前后不过短短五天!人常说,于是之办事优柔,我要说,谬也!于是之是个有肩膀头的爷们。 中小学生语文题库,中小学学生语文试卷,就来<A hTtps://www.euzW.net/yuweNtiku/>易优语文题库</a>。
是之希望我早日出作品,我则要求给予充裕的时间,实现由戏曲向话剧的“转轨”。他问,“多久?”我说,“两三年吧。”“能不能短点?”“努力。”事后偶尔碰面,他又问,“写了吗?”我说,“不是说好……”他狡黠一笑,“哦,忘了,不过,有了构思无妨谈谈,大家帮着出出点子。”我怀疑他的记性,感激他的好心,这叫大智若愚!
转年初夏,我怀揣《李白》初稿,忐忑着轻敲他的办公室,他正开会,我抱歉地说,“只要一分钟……”他走到门外,小眼睛闪烁睿智,“有了?”我点点头。“写什么的?”“李白。”“我来!”他未看剧本就表态,分明是在鼓励我。“就是为你写的!”我也机敏起来,舌灿莲花。半个月后,是之约我共进工作午餐,不是二人,是三人,导演苏民介入了。从迷惘彷徨到云破天开,恍惚转瞬。
一个艺术家的好品德贯穿于艺术行为的全过程之中。当我怀着感激之情回顾人艺对《李白》的经营的时候,我每每为是之的付出所感动。无论是艺术管理的理念,还是艺术创作的思维,都给人启迪。有一天,老于说,“我琢磨《李白》应有自身独特的形式,反正跟杜甫不一样,应该空灵一些。咳,我也没想好,我这是难为作者了!”啊,空灵……太对了,也太难了!我为此犯晕,辗转反侧好几晚,为了《李白》空灵,我可是一点也不空灵。 作文能力提升,就来易优作文,https://www.euzw.net
反复最多的是全剧的高潮 ——李白与妻子分手,一种情投意合的最后诀别。“最后诀别”的必然性与“情投意合”的暂住性形成强烈的冲突,这正是戏剧性之所在!我和导演为这番发现而樽俎交欢。没想到老于看后却不满意。我懵了。又过了几天,老于说他又看了几遍,觉得似乎也只能这么写,他原先的意见收回。我又懵了! ——我作剧几十年,遇到文化官员无数,愣是没有听说过哪位说过“意见收回”的话!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老于看第一遍不满意,而后觉得还可以?其间有无直觉与思考的参差?戏剧流程不允许“思维暂留”,观剧自是“一次完成”,怎能奢望观众再看三看?我终于从老于的第一次直觉中悟出了毛病,于是,改!……
啊,是之对我、对《李白》应该不是特殊关照。他有平民意识、平民视角,从来一视同仁。他长期领导创作,言论颇多警策。 作文能力提升,就来易优作文,https://www.euw.net
他说:“作品不是什么人抓出来的,而是作者写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不好颠倒了。”“要平等待人,尊重他们的劳动。要肯于承认自己不如作者,至少在他所写的题材上,你不如他们懂得多。”
好些年前,我做过一个梦,我的戏上演了,我握着老于的手哭了,哭得很伤心,竟哭醒了。我很纳闷,我发表过近百部剧本,多半上演了,何以“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注】于是之: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
(1)下面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5分)
A.文章在娓娓的叙述性语言中穿插一些精要的议论语句,使传主的精神风貌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B.文章结尾处详写梦境,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艺术地表现了“我”因剧本难以上演,愧对于是之的复杂感情。
C.“更有文化层面的惆怅”,把作者难以言喻的心酸具体化,意在说明于是之舞台形象的渐行渐远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 易优作文批改系统,易优作文打分、易优作文评分评价 <a href=https://wwW.euzW.net/jiaoshoulanmu/>易优作文批改</A>
D.“于是之是个有肩膀头的爷们”,语言诙谐中又有赞叹,写出于是之先生性格中勇于担当的一面。
E.为了突出于是之先生深厚的艺术修养,作者详写“我”创作《李白》剧本时,于是之先生给予我大量的指点与帮助。
(2)依据文意,理解下列画线内容在文中所包含的深意。(6分)
①“我来!”
②作品不是什么人抓出来的,而是作者写出来的。
(3)作者为什么说“自从熟悉了于是之,我情愿回归荒诞的史学经典”,请结合传记内容加以简析。(6分)
(4)关于《李白》剧本的修改,作者写道:“我终于从老于的第一次直觉中悟出了毛病,于是,改!”你怎样认识文中所说的“直觉”和“思考”。(8分)
答案:
12.(1)BE(B项“愧对”的情感不当,E项写于是之先生帮助我,一是写其艺术修养之高,一是写其光明磊落的领导胸怀,侧重于后者)
作文能力提升,就来易优作文,https://www.euzw.net
(2)①从上下文内容看,简单的“我来”,包含着于先生对“我”的鼓励,两个字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于先生对剧本的态度(3分)。②体现了于是之先生对话剧艺术的尊重,对话剧创作者的尊重(3分)。
(3)因为作者在与于是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于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1分)也是一位富有艺术管理理念、具有高超艺术创作思维的管理者。(1分)他对话剧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关心并鼓励创编人员的成长,尊重艺术,尊重编剧,敢于担当,光明磊落。(具体展开4分)(回答此题要抓住句中的“熟悉”“情愿”二词)
(4)我认为文中的“直觉”和“思考”存在着密切联系(1分)。“我”从艺术创作的规律出发,思考于先生的意见,并最终进行了修改,是因为“我”认为,虽然于先生对剧本修改态度前后不一,但从“我”对于先生的了解中,我知道,于先生的“直觉”源于他曾经的对艺术的深入思考,正是因为思考的深入,才会在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身上体现了过人的“直觉”,也才会对剧本提出最初的修改要求,以至让“我”发“懵”(4分)。从文本中体现的“直觉”和“思考”的关系中,我懂得,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方向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科学的思考之后,往往可以形成对问题的直觉反映,这种直觉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自然反映。(3分)
——(记叙文阅读理解)《好人是之》阅读答案,来自易优作文网,转载请注明出处。学作文,学阅读,提升语文阅读写作能力,就来易优作文。
《(记叙文阅读理解)《好人是之》阅读答案》添加时间:2024-12-13;更新时间:2025-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