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录后畅享更多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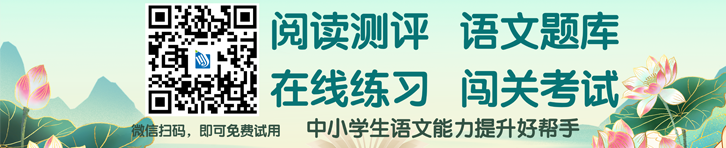
青年作家郗晓波说过,卡夫卡的《变形记》把我们带往不熟悉的另一世界,而其实,那另一世界原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只是卡夫卡试图用另一套叙述方式与技巧来展示我们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
因为我们平时不朝它看上一眼,初见之下,才会感到它是如此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像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探究存在之谜的,但他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可视的内心生活”--人的内心同样作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存在。
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他冷峻的眼光聚焦的是“真”。在他看来,“真”若要体现,就必须借助于“丑”。于是《变形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丑陋的意象,卡夫卡毫不客气地放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似乎他觉得丑就是丑,甚至根本没必要用美作为小说结束之前的一点安慰。所以,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卡夫卡也没有让这些丑陋的意象从背面发出一点美的光芒。 提升作文素养,寻找作文素材,就来<A httpS://www.Euzw.net/yuwEnsuyang/>易优作文素养</a>。
《变形记》创作于1912年,当时,批判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这个原本含辛茹苦撑起一个家庭的男人突然变成了一家人的累赘,不仅父母对他极度厌恶,甚至平时岁疼爱的妹妹也逐渐对他产生了不满,进而抛弃了他。最后,这一家人竟因为格里高尔的死获得了解脱,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卡夫卡想用这个故事努力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利用与被利用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个基础失去,或者二者之间对应关系发生变化,本来看似稳固的人际关系就会迅速瓦解。着也许令为数众多的理想主义者难以接受,但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被卡夫卡发现了,而整个故事正体现了“表现论”的实质--把描写对象“陌生化”,造成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距离,从而引起惊异,迫使人从另一个角度探悉同一事物的本质,即“离间”。卡夫卡通过“离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同他一样,重新思考,发现这个“被习俗观念掩盖”的事实。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对社会中人的放逐与被放逐同样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所有人都不能接受格里高尔甲虫的形象,听不懂他的语言,不理解他的行为。这就意味着格里高尔是被放逐的。而在变形后,格里高尔不吃人的食物,抛弃人的行为习惯,这是他对自己的放逐,或者说是他对其他正常人的放逐。在卡夫卡看来,一个人的思想、形骸不被他人所接受,其后果必然是这个人与其他人的相互离弃。卡夫卡明白:人与人是不相通的;但是,“人的骨子里渴望别人的关怀和爱心”。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可是仍然“赶忙爬到自己的房间门口,蹲在门前,好让父亲从客厅里一进来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儿子乖得很,一心就想立即回自己的房间,根本不需要赶,要是门开着,他马上就会进去的”。但是,所有的美好愿望以及善意的行为,只换来一只重创自己的苹果。对这件事的描述说明:人与自己,与别人相离异,但是同时仍在努力地、白费力气却令人感动地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要“好歹指掇起灵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只甲虫。往往能够正视卡夫卡个人的许多人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易优作文网名师改作文(https://wWw.euzw.net/jiaoshoulanmu/ ),易优作文评分系统,易优作文打分系统。
卡夫卡曾说:“我在自己家里比陌生人还陌生。”可以这样认为:这充分暗示了卡夫卡自己与小说主人公命运的相似之处。虽然这些相似远不能证明这是一篇自传,但是作者本人与格里高尔的对应从他生前的一些琐事中亦可见一斑。根据自己勒戒一番,卡夫卡的日记中这样写到“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着。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而《变形记》开头对格里高尔的工作的描述正是卡夫卡当时工作状况写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卡夫卡与身边的人总是相处得很好,给别人留下愉快阳光的印象;但是,从他的日记和与勃罗德等人的信以及部分文字中,我们才能看到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这个观点在《卡夫卡传》中就已提出来。在《变形记》的第三部分,卡夫卡运用大量篇幅描写格里高尔垂死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作。
易优作文网名师改作文(https://wWw.euzw.net/jiaoshoulanmu/ ),易优作文评分系统,易优作文打分系统。
“格里高又向前爬了一段,将头和地板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以便和房客们的眼光相遇。他想,他要是一个甲虫,音乐能如此感到他吗?他好像觉得再往前爬就是朝看见了的、但不认识的食物那儿爬去。他决定向他妹妹那儿爬去,在他妹妹的裙子上拉扯,暗示她应该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因为她不值得替他们演奏,这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感谢这种演奏,他不会让她再走出他的房间,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让她再走出他的房间。他的令人可怕的外形第一次发挥了作用,他要出现在他房间的各个门边并且向不满意小提琴演奏的房客们发出怒吼。妹妹不是被迫地,而是自愿地留在他格里高身边,她会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倾听他的意见,他也愿意向她提供自己的看法,他就曾经毫不动摇地要送他妹妹上音乐学院深造。要不是发生这种倒霉的事,他肯定在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吗?向大家宣布他的决定,而不考虑任何反对的意见。宣布以后,妹妹一定激动得泪流满面。我要站起来吻她的脖子,她自从到公司工作以来,脖子上既无衣领,也无饰带。”
在线批改作文,<a href=https://www.euzw.net/jiaoshoulanmu/>易优名师作文批改</a>
“他又开始了!这时她甚至以一种使格里高莫名其妙的吓人动作离开了母亲,从沙发上走开了,好像宁愿让母亲去牺牲,也不愿意坐在格里高的旁边,她急匆匆地走到父亲后面,由于她的表现,父亲也激动起来,也站起来了,将手臂抬起了一半以示保护妹妹。格里高根本没有想去吓唬谁。他只是开始爬回自己的房间,而这些动作又很显眼。因为他很痛苦,拐弯的时候头部必须帮助进行。他好多次将头抬起来,又磕在地板上,他停下来扫视周围,大家似乎都很明白他要爬回自己的房间,那实在是一个可怜的时刻。大家沉默而伤心地看着他。”
“他的背碰到了腐烂的苹果,苹果的霉烂点波及周围。他带着爱心和感动回忆家庭,并坚定地认为他必须从这个家里消失,这种看法的坚定性比起他妹妹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他陷入了空洞而安静的沉思。教堂已第三次敲响了晨钟,黎明开始了,他正经历着窗外破晓的时光,他的头无意识地完全地低垂,他已经鼻息奄奄了。”这样显得非常拖沓。但正是这样的拖沓描绘了当时的情形渲染了故事深灰色的感情基调。甚至,这对抒发作者的同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猛士,卡夫卡在与自己的生活不断抗争后,却陷入了更残酷的生活境地。正如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一样,卡夫卡中年时的处境同样无可就药。卡夫卡自己也是不被别人理解的,所以他同情格里高尔。于是,他为格里高尔安排了死亡的结局。他清醒地发现,除非死亡,悲苦的命运才能得到改变和解脱,才能不用这样痛并爱着,不用面对人情的逐渐淡漠。
在线批改作文,<a href=https://www.euzw.net/jiaoshoulanmu/>易优名师作文批改</a>
这也许是作为凡人的卡夫卡能够为自己安排的。
高二:刘妙真
学作文,学阅读,提升语文阅读写作能力,就来易优作文。作文点评、作文精批、作文修改润色,就来易优作文。
《痛并爱着》添加时间:2024-12-15;更新时间:2025-08-06
推荐课程
- 1苏州初中语文培训_2025暑假初中语文集训班_吴中初中语文暑...
- 2苏州作文培训_小升初语文衔接班(阅读写作培训2025年暑假班...
- 3新初三暑假语文阅读写作集训班(B)_初中语文阅读写作直播课—...
- 4小学中年级语文阅读写作直播课(周日晚)_小学语文阅读写作直播...
- 5小学高年级语文阅读写作直播课(周六晚)_小学语文阅读写作直播...
- 6苏州吴中小学数学学习能力提升班(周末常规班)_苏州小学数学培...
- 7苏州吴中暑假初中数学衔接班_初中数学思维训练_初中数学培训_...
- 8苏州吴中暑假小学数学学习能力提升班_小学数学培训_小学数学辅...
- 9苏州少儿书法培训_易优少儿书法暑假集训班_小学生铅笔字培训_...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