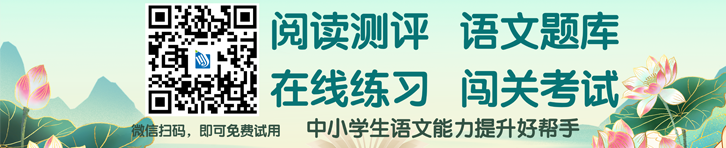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的闺怨诗中,有不少诗作是出自男性之手。这些男性诗人或以女性的身份和口吻代女性立言,或从男性主体的角度叙写闺阁中的女性。但无论从那个角度入手,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女性不幸遭际和命运的同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抒写了闺阁女性郁积在胸的孤苦与幽怨。因此,有人把此类诗称之为“男性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但是,任何一个男性诗人,他毕竟不是女性,所以他无法进入女性的经验世界中,女性独特的个人生活空间、独有的女性感觉和生理心理体验等,都是男性诗人所无法体察的。所以男性诗人闺怨诗中的女性形象,无疑都是男性主体异己的想象,她们被自觉不自觉地纳入了男性文化的历史编码中。盛唐诗人王昌龄是男性诗人中写闺怨诗的高手。他最为著名的《闺怨》一诗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主义文本。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的开头两句完全是从男性的视点来写女性的。后世的诗论者在分析这首诗时,同诗人一样,也总是无一例外地把第二句“春日凝妆上翠楼”中的“凝妆”作为首句“闺中少妇不知愁”的证据来加以解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女为悦己者容”,一旦作为“悦己者”的男性(主要是指丈夫)不在眼前,其化妆的意义便不复存在。“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因无男性欣赏,女性不必为悦己者而容,“懒妆”应是那些独守空闺的少妇们惟一理想的形象。而诗中的这位闺中少妇,丈夫离家出征,不在眼前,还浓妆艳抹,恣意梳妆,分明是不知愁滋味。这完全是以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的结果,女性始终被置于一个“被看者”的客体地位。男性中心主义者认为,女性是属于男性的财产,一个女人的价值只能为一个男人奉献,其美丽的一面也只能留给其男性主人公欣赏,一旦爱慕他的男性远离,其美色便暂时失去了意义。更有甚者,一些男性甚至还对他离家后女性行为、妆梳都要做出许多规定,比如不准化妆、不准外出等等,以免引起其他男人的非分之想。他们如同保扩自己的财产一样,保护自己的性特权。不然,男人出门在外,怎能放得下心呢?
王昌龄作为一个男性作者,在叙写闺阁中的女性形象时,带着一种处于社会性别支配地位的优越感,因而与女性抒情主体在内在感情上处于游离状态,很难做到水乳交融,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带有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色彩。他认为,闺中少妇“凝妆上翠楼”是“不知愁”的表现。在我看来,女性形象固然可以作为男性主体审美的对象,但女性毕竟不同于花花草草之类的自然审美客体,她兼有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可迎合男性审美的需要,给男性以愉悦之感,同时愉悦自己。另一方面,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当女性容貌衰减时,也会影响女性自己的心态。因为容貌衰减,即意味着女性资本受损,直接关联女性生存功利的大计。女性一旦有此忧虑,便会特别注意外在的修饰。君不见,甚至到了当今社会,不少女性,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对美容、减肥、隆胸等还趋之若鹜,甚至为此遭罪受苦,仍乐此不疲吗?你固然可以说这是女性爱美悦己的一种表现,但仔细玩味,你便不难发现这种“爱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男性欲望化的审美眼光。这种修饰本身正是女性内心忧愁的一种表现,其中隐含着种种无奈和难言之隐。它折射出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生命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摧残。《闺怨》一诗中的女主人公的“凝妆”,或许正是她“知愁”的一种表现,她生怕将来觅得了“功名”后的丈夫厌弃自己,到时自己岂不由眼前的“怨妇”变成“弃妇”?
另外,她的登楼赏春之举也正是她“知愁”的一种外在表现。独守空闺,孤灯只影相伴,自然寂寞,何况还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少妇,更应该是寂寞难耐了,故才有登楼赏春之举。她是想借此举来散散心,驱解心头的忧愁苦闷。可谁知此举犹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未曾料及“忽见陌头杨柳色”,反倒惹起一腔幽怨。“杨柳”乃陌上常见之物,何以能如此触动少妇的情怀呢?这恐怕和杨柳被我们中国人赋予的文化内涵及杨柳本身的形态特征有关。杨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更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因柳与“留”谐音,古人有折柳相赠的习俗。诗中的这位少妇由于丈夫的远离,生理与心理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情感上处于一种严重的缺失状态。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处于严重缺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状态中,对极微弱的外界刺激也会有敏感的反应,并且当个体无法消解这种种缺失时,想象力往往会变得异常活跃。加上杨柳下垂的形状及其柔软性与人悲哀的心理结构具有异质同构性或结构上的相似性,因此当这位闺中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或许会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依依深情,想到戍守边关的丈夫此刻可能正奋战在黄沙漫漫的疆场,想到杨柳易衰、青春易逝,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想到丈夫不在家,自己孤灯青帐、独枕难眠的日日夜夜……想到这一切,少妇郁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伤感便一齐涌上心头,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后悔当初“夫婿觅封侯”时自己没有阻拦,甚至还默许了。可如今一切都已是既成事实,留下的只有千般悔万般怨而已。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忧愁,杨柳是不会引起她愁怨的心理反应,也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闺中少妇”并非“不知愁”或“不曾愁”。试想,作为一个曾经与丈夫卿卿我我、夫妻恩爱的少妇,丈夫远征他乡,自己独守空闺、形影相吊,其寂寞愁苦,自不待言。说她“不知愁”或“不曾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站在局外人——(易优作文,专注中小学生语文阅读写作能力提升)男性主体的位置观照的结果。当然,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闺中少妇”可能把自己的愁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然过多的表露,不知又会被那些男权文化的操持者加上何等的“罪名”。
唐代前期国力强盛,边疆战事频繁,从军远征、猎取功名,成为当时男人们“觅封侯”的一条重要途径。“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成为当时许多人的生活理想,甚至成为一种时代风尚。然而求得功名、平安而归的毕竟是少数男人,更多的男人则战死疆场。于是,不少留守家中、独守空闺的少妇便成了男人们求取功名的牺牲品。“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两句诗便是那些不幸女子苦难生活的生动写照。男人们只想着自己成就功名,可曾想过女人的需要?不要说为什么保家卫国,也不要说为了什么小家庭的未来,男人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掩藏不住其内心的自私与虚伪。说什么是女人叫丈夫去“觅封侯”,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卑微的身份和地位,怎能左右男人们的决定和选择呢?至多只是用女人的柔情,温暖男人的心,用女人的缠绵,延缓男人的行动而已。因此,如果说诗中这位少妇有后悔,那也只可能是后悔当初没有用自己的柔情蜜意笼住男人的心,让他放弃“觅封侯”的念头,而是默默地顺从而已。
一般来说,“在男性的话语的“牢笼”中,女性是无法建立自己的话语家园的。因为她们在不断的被叙述时只能为男性提供意义而得到意义反馈,这是主客体之间因为性别差异和权利不等而出现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立关系”(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身处男权社会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王昌龄也没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点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因而表现出来的不可能是女性主体真实的生命状态,而是男性话语中的闺阁女性形象。
《男性话语中的闺阁女性形象_高中语文基础知识》由易优作文网(www.euzw.net)收集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文培训,作文投稿,阅读写作能力提升,就来易优作文。